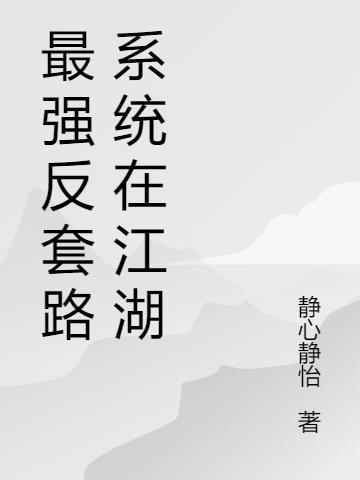第1章 暴雨惊变
冰凉的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,苏明远猛地睁开眼。
不是图书馆霉味混杂着咖啡香的空气,而是浓重的泥土腥气和腐烂稻草的味道,粗粝的麻布摩擦着他的手臂。
他挣扎着想坐起,后脑传来撕裂般的剧痛,掌心下意识地按向额头,却触到一道陌生的、微微凸起的浅疤,横在左眉骨上方。
“明远!我的儿!你可算醒了!”一个嘶哑、带着浓重哭腔的声音撞进耳朵。
苏明远艰难地转动僵硬的脖颈。
昏暗摇曳的油灯光晕里,映出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黝黑、干瘦、布满刀刻般的皱纹,浑浊的眼睛里盛满了惊惶和一种近乎绝望的关切。
这是谁?
他最后的记忆是图书馆窗外撕裂夜空的闪电,指尖滑过《宋史·食货志》冰冷的书页,上面记载着北宋熙宁年间沉重的夏税…然后就是一片混沌的黑暗,和此刻全身骨头仿佛被拆散的剧痛。
轰隆!
一道惊雷炸响在低矮的茅草屋顶,惨白的电光瞬间照亮了这间逼仄、破败的泥屋。
泥糊的墙壁斑驳脱落,屋顶漏下的雨水在泥地上汇成浑浊的小洼,角落里堆着几件磨损得看不出原色的农具,空气里弥漫着湿冷、贫穷和绝望的气息。
这不是梦。
苏明远的心沉了下去,一股冰冷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。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,拇指无意识地、用力地着指腹——那是长期握笔、敲击键盘留下的肌肉记忆,此刻却成了他与那个消逝世界的唯一微弱连接。
“爹!爹!税吏…税吏又来了!堵在院门口了!”一个带着哭音的、属于少年的呼喊穿透了哗啦啦的雨声和呜咽的风声,猛地撞开虚掩的、吱呀作响的破木门。
门口冲进来一个浑身湿透、单薄得像秋天芦苇杆的少年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,惊恐地看着苏明远,又转向那个被称作“爹”的男人。
爹?苏明远?北宋?湖州?农户?
几个破碎的词带着冰冷的铁锈味,狠狠凿进苏明远混乱的脑海。
“快!快扶我起来!”那黝黑干瘦的男人——苏明远这具身体的父亲——猛地从苏明远床边的小凳上弹起,动作因为惊惶而踉跄。他胡乱地抹了一把脸,不知是要擦掉雨水还是别的什么,浑浊的眼里只剩下一种被逼到悬崖边的恐惧。
苏明远被那个叫苏砚的少年和父亲合力搀扶着,几乎是半拖半抱地挪到了堂屋门口。
屋外,暴雨如注,天地间一片混沌的灰白。
院门那扇破旧的柴扉在风雨中可怜地摇晃着。
门外,三个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的身影如同铁铸的凶神,牢牢钉在泥泞里。
为首那个身材粗壮,斗笠压得很低,雨水顺着粗糙的蓑衣边缘成串滴落。他一只脚粗暴地踏在门槛上,手里一根裹了铁皮的硬木棍,正不耐烦地敲打着门框,发出沉闷而咄咄逼人的“梆梆”声。
“苏老蔫!”粗嘎的吼声盖过了风雨,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,“拖!再给老子拖!夏税!三石三斗!一粒也不能少!今天要是见不到粮,老子拆了你这破窝棚,拿你婆娘去抵债!”
苏明远感到搀扶着自己的父亲浑身剧烈地一抖,那只抓着他胳膊的、布满厚茧和老茧的手猛地收紧,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。
“差…差爷!”父亲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带着哭腔和深入骨髓的卑微,“求您…求您再宽限几日!这雨…这雨下得邪性,田都淹了…麦子…麦子全泡在水里,还没熟透啊…实在…实在拿不出…”
“少他娘的废话!”税吏头子猛地扬起手中的硬木棍,作势要打,“天上下刀子,该交的税也得交!王相公的新法,懂不懂?青苗贷你们这些穷骨头没少借吧?这时候装什么可怜!”
棍影带着风声落下。
苏明远瞳孔骤缩,一股源自现代灵魂的本能愤怒瞬间冲垮了穿越带来的眩晕和恐惧。
他想要冲上去,身体却虚弱得一个趔趄。
然而,他身边那个干瘦的身影比他更快。
“噗通!”
沉闷的、肉体撞击泥水的声音。
父亲竟首挺挺地朝着院门的方向,重重地跪了下去!
浑浊冰冷的泥浆瞬间淹没了他枯瘦的膝盖。
“差爷开恩!开恩啊!”他佝偻着背,额头死死抵在冰冷的、混杂着碎石和草梗的泥水里,发出沉闷的哀求,“粮食…粮食是真没有…我…我这条老命…您拿去…求您放过我婆娘和孩子…”
雨水无情地冲刷着他花白凌乱的头发,紧贴在他枯槁的脸上。
那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姿态,像一把烧红的烙铁,狠狠烫在苏明远的视网膜上,烫进他来自另一个平等世界的灵魂深处!
一股前所未有的、混合着荒谬、恶心和滔天怒意的血气猛地冲上头顶!什么穿越的迷茫,身体的虚弱,瞬间被这股烈火焚尽!
“爹!起来!”苏明远喉咙里挤出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,却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陌生的、斩钉截铁的强硬。他挣脱苏砚的搀扶,用尽全身力气,一步踏进门口冰冷的积水中,挡在父亲和那狰狞的棍棒之间。
冰冷的雨水兜头浇下,让他滚烫的头脑为之一清,属于历史系研究生的记忆碎片在电光石火间飞速拼合——北宋,湖州,蚕桑重地,“以绢折税”的传统…
“差爷!”苏明远迎着税吏头子惊愕而凶狠的目光,雨水顺着他苍白却异常沉静的脸颊流下,汇聚在下颌,滴落泥泞,“麦田己毁,强征无益!湖州自古桑蚕丰饶,官府亦有以绢帛折抵夏税的旧例!我家愿改种桑树,待秋蚕成茧,必以足额上等湖丝抵税!绝不拖欠分毫!”
他的声音不高,却异常清晰,穿透了哗哗的雨声,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赤贫茅屋的冷静和笃定。
三个税吏明显愣住了。
为首那个眯起眼,斗笠下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苏明远年轻却毫无惧色的脸,又扫过他身后泥水中瑟瑟发抖的老农和惊恐的少年。
“改种桑树?以丝抵税?”税吏头子嗤笑一声,木棍在泥水里不耐烦地杵了杵,“新鲜!老子收税十几年,头回听这屁话!你算什么东西?祖制!懂不懂?田赋就是田赋!就得交粮食!变祖宗章法,你有几个脑袋?”
就在这时,一个苍老却极具穿透力的怒喝,如同炸雷般在暴雨中响起:
“放肆!”
众人循声望去。
只见村中方向,两个健仆撑着一把巨大的油纸伞,簇拥着一位须发皆白、身穿绸缎长袍的老者,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走来。
老者脸色铁青,正是苏氏一族的族长苏承宗。
他看也不看跪在泥水里的苏父,凌厉如鹰隼的目光死死钉在苏明远身上,仿佛要将他刺穿。
“苏明远!你这孽障!昏了头了?”族长手中的拐杖重重顿在泥水里,溅起一片污浊,“祖制煌煌,田赋纳粮,天经地义!你竟敢妄言‘以桑代赋’,蛊惑视听,动摇根本!谁给你的胆子?想让我苏氏一族都背上违逆朝廷、不敬祖宗的罪名吗?!”
他胸膛剧烈起伏,显然气得不轻: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!再敢胡言乱语,惑乱人心,莫怪老夫开祠堂,请家法,将你这忤逆子逐出宗族!”
冰冷的雨水顺着额发流进苏明远的眼睛,带来一阵刺痛。
他看着族长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,看着税吏脸上毫不掩饰的嘲弄和凶狠,再低头,看着泥水中父亲那卑微如虫豸、因族长到来而更加绝望颤抖的身影。
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冷的怒意在他胸腔里冲撞。
祖制?天经地义?
不过是压在万千生民脊梁上,吸吮骨髓的枷锁!是这吃人礼教冠冕堂皇的借口!
他攥紧了拳头,指甲深深陷进掌心那层不属于他的、属于这具身体常年劳作的厚茧里,却感觉不到痛。只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、对这个时代的剧烈排斥和愤怒在灼烧。
最终,他什么也没说。只是沉默地、用力地弯下腰,试图将泥水中几乎的父亲搀扶起来。
冰冷的泥水浸透了他单薄的衣衫,寒意刺骨。
税吏头子见状,发出一声冷哼,丢下一句“三天!最后三天!看不到粮食,等着吃牢饭吧!”便带着手下骂骂咧咧地转身,身影很快消失在灰茫茫的雨幕里。
族长苏承宗厌恶地扫了一眼泥泞中的父子俩,仿佛多看一眼都脏了眼睛,在健仆的搀扶下,也气咻咻地转身离去。
破败的小院,只剩下暴雨无情的冲刷声,和苏父压抑的、绝望的呜咽。
苏明远沉默地将父亲和苏砚扶进屋内。草草擦干身体,换上仅有的、打着补丁的干爽旧衣。
昏暗的油灯下,苏父佝偻着背,坐在吱呀作响的破凳上,双手深深插进花白的头发里,肩膀无声地耸动着。
苏砚红着眼圈,默默收拾着屋里漏雨的盆罐。
苏明远的目光落在墙角一个半开的、满是虫蛀痕迹的旧木箱上。箱盖下,压着一本边角磨损、纸张泛黄发脆的册子。
那是苏家的田赋账册。
他走过去,拿起那本沉甸甸的册子,就着昏暗跳动的灯火翻开。
粗糙发黄的纸页上,是父亲歪歪扭扭、记录着历年田亩、收成和税赋的字迹,浸染着汗水和卑微。
他修长的手指带着一种属于研究者的冷静,快速划过那些代表苦难的数字。
去年,苏家实有田七亩三分,夏税征麦两石五斗。
今年,账册上登记的田亩数依旧是七亩三分。
但税吏口中的夏税,赫然变成了三石三斗!
苏明远的手指顿住,眼神瞬间锐利如刀锋,穿透昏黄的灯光。
三石三斗!
比去年凭空多出整整八斗!近三成!
这绝不是正常的“加耗”或“折变”能解释的!
他的目光如鹰隼般向下搜寻,掠过自家那串刺眼的数字,落在记录着村中另一大户——钱员外家的条目上。
钱府名下田亩,去年登记在册的是良田一百二十亩。
而今年,那墨迹稍新的数字,竟赫然写着:一百一十五亩!
减少了五亩?
苏明远的心猛地一沉。
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北宋,豪强只会想方设法隐匿田产、偷逃赋税,绝无可能主动减少田亩数!
除非…这减少的五亩,是以某种“合法”的方式,转嫁到了他们这些无力反抗的贫户头上?
他指腹用力捻过账册上“钱府”二字旁那异常工整、与父亲笔迹截然不同的墨迹,一个冰冷的名字浮上心头——钱府的账房先生,赵魁。
每次登记造册,都是此人经手!
窗外,一道惨白的闪电再次撕裂雨夜。
瞬间的光亮映亮了苏明远年轻却沉凝如水的脸庞。
他额角那道新添的浅疤在电光下微微反光,湿漉漉的额发垂落几缕,其中一缕,在闪电的映照下,竟透出一种近乎妖异的、不自然的银白。
那是时空撕裂刻下的印记。
他垂下眼睑,遮住了眼底翻涌的冰冷怒意和洞悉一切的精光。
指尖无意识地再次着右手拇指指腹那层薄茧——一个来自异世的灵魂,在北宋风雨飘摇的寒门茅屋中,第一次真正看清了眼前这头名为“不公”的狰狞巨兽。
暴风雨拍打着脆弱的窗棂,屋内的油灯火焰被涌入的冷风吹得疯狂摇曳,将苏明远沉思的身影长长地、扭曲地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。
那影子沉默着,却仿佛蕴藏着即将破土而出的惊雷。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