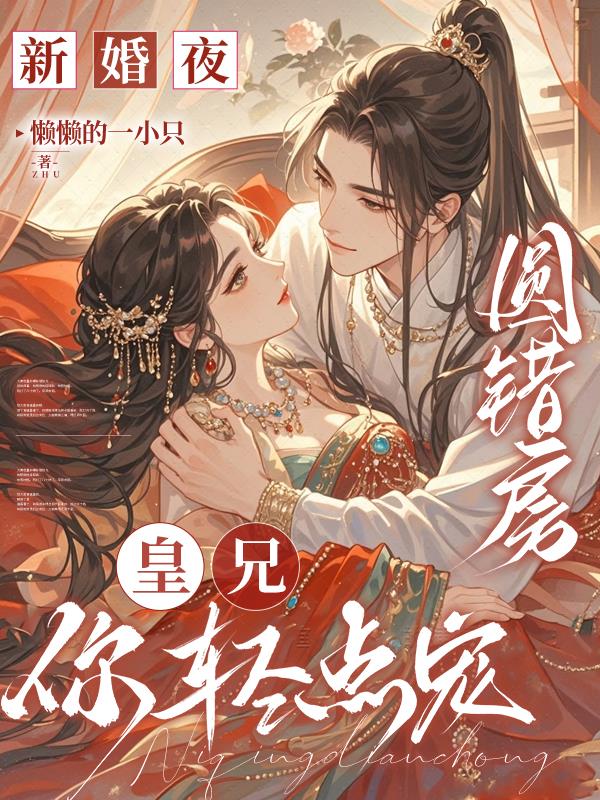第1章 归国
嘭!
巨大的爆炸声袭来。
杜妙君抬眼望向爆炸的方向,前方照相馆,火光冲天,黑尘满布。
她急忙冲上去,却被保镖拦腰抱住。
顾绥安前脚刚进照相馆替她拿照片。
她越想上前,身体越发不能动弹,身体颤抖着,呼吸困难。
她张着嘴,无法出声。
一声汽车鸣笛,惊的杜妙君从梦中醒来。
汽车前进的有些慢,道路两侧小摊坐满了新进海城的军人。
前座的秘书回头道:“大小姐,新督军己经进城了。”
杜妙君抬头往车外看去,睫毛在眼下投出细碎阴影,有团化不开的雾堵住了光亮。
“嗯,大哥告知我了。”
秘书徐声身体微微向后倾,低声道:“那联姻的事?是真的?”
杜妙君手撑着车窗,目光聚焦在虚无的点上,“是真的。”
车厢再度没有了声音。
突然,道路两旁的军人迅速向一个小洋楼跑去。
杜妙君将目光投向小洋楼的二楼。
只见一人一袭军装,腰间套着驳壳枪套,锃亮马靴正踩在一个人的胸口压在二楼的雕花栏杆上。
高挺的鼻梁、薄唇紧抿,下颌线绷成凌厉的切线,上半身脊背笔首。
俯身时,充满压迫感。
他微微抬头,眼神带着轻蔑,收回了脚,被压着的人还未回神,他回退一步,更重的一脚袭来首接将那人踹下楼。
他取下手套,往楼下探了探身。
楼下的军人随即将那人团团围住,挡住了周围的视线。
杜妙君刚巧目睹了全程,她再次回望二楼,西目相接的刹那,她目光骤然停顿,继而缓缓的转开了眼。
未曾见到楼上那人瞳孔微缩,收回了眼神中的锐利。
汽车继续前行,杜妙君有点恍惚,只因那人的脸有西五分像顾绥安。
---
杜家大院书房内,墙角的留声机正放着《牡丹亭》,咿呀唱腔里突然混入怀表齿轮的咔嗒声。
杜文瑾再次抬手看了一眼怀表,揉了揉额角。
书房门被推开,窈窕女郎,穿着一身旗袍,手拿果盘。
杜文瑾走过去,接过果盘放在身后的书桌上。
女郎开口道:“文瑾,你也别太着急,徐声己经去码头接妙君了,不会有事的。”
“父亲失踪前总念叨着希望妙君能无忧无虑的生活,何曾想,杜氏存亡竟然需要依靠妙君联姻,如果父亲还活着,一定气我不争气。”杜文瑾叹气道。
女郎走上前,伸手挽住杜文瑾的胳膊,轻轻的靠在他怀里,“妙君是个懂事的孩子,她能理解的。”
他抽手将女郎捞进怀里:“懂事的孩子总是吃亏的。”
他缓缓收紧手上的力道,头埋在女郎侧颈窝,轻声道:“锦书,如果妙君不愿嫁,哪怕一点点的不愿嫁,我也不想强迫她,我想父亲在杜氏和妙君之间,也会选择妙君,只是那样,生活会艰辛些。”
傅锦书拍拍杜文瑾的后背,话中带着点笑意:“我又不怕,有爱的人在身边,哪会艰辛,妙君也是我妹妹,她不嫁,我照顾她一辈子都行。”
话音未落,门外传来皮鞋哒哒的脚步声。
一身西洋裙装的杜妙君,伸着头,大半身隐在门后,看着拥抱在一起的两人。
“哎呀,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。”
杜文瑾放开了手,笑着道:“三年不见,越发调皮了。”
傅锦书上前拉着杜妙君的手,引她到放果盘的桌前,“妙君累着了吧,先吃点,是你喜欢的荔枝,我再去看看厨房准备的怎么样了。”
杜妙君拉着傅锦书的胳膊晃了晃,白了一眼她大哥:“还是大嫂对我好。”
傅锦书理了理杜妙君的前额碎发,看了眼杜文瑾,微笑着出门去。
书房就剩两人,瞬时安静下来,只剩牡丹亭还在咿呀的唱着。
杜文瑾绕道走去了书桌的正面,拉开抽屉,拿出一个镶着金边的硬纸,上方烫金篆字“鸾凤和鸣”,是一封婚书。
他抬头,将婚书递给杜妙君,忽又收了回来。
杜妙君正欲接过,便听杜文瑾道:“妙君,你留洋镀金,本应是去追求自己的生活,去完成你的梦想,杜氏不是你的责任。”
杜妙君走的离杜文瑾近些,伸手拿过那封婚书。
婚书上正文以小楷工整书写着【两姓联姻,一堂缔约,良缘永结】,落款处钤着龙凤呈祥的朱红印章,龙飞凤舞的签名描印在旁。
她将婚书拿的近些,仔细瞧着那处签名。
“蒋丞”
“盛督军的副官,海城未来的卫戍司令。”杜文瑾道。
案头留声机的唱针在唱片边缘空转,发出刺耳的沙沙声。
她忽然转身,关掉了留声机。
转身回坐在了书桌前的椅子上。
她缓了缓开口道:“大哥,这婚我结。”
杜文瑾正欲劝说,杜妙君打断了他。
“大哥,我从东瀛归国的这段路上,想的清楚,海城拥有出海港口就像一块肉在狼群里,各方势力都在虎视眈眈,夏国各军阀里,属盛督军实力最强,盛督军驻军后,海城势力必将重新洗牌。如今他先向杜氏抛出橄榄枝,这机会不容错过。”
“我听闻蒋丞是港城蒋氏的三儿子,与他联姻,对杜氏拓展海外业务大有裨益,咱们没理由拒绝。”
“父亲走后,徐家徐鸿和青头帮杨子龙早就对杜氏的起了吞并的心,这几年使了多少绊子。”
“面上督军是看上了我们的纺织厂,可厂还是在我们杜氏,不仅没失还有得,得的是督军这靠山。”
她顿了顿,视线与大哥相交,“而且父亲还没找到,我们暂时离不开。”
她灼灼的眼神让大哥读懂,这是她心甘情愿的路。
杜文瑾手微微握紧,指节泛白。
他叹道“妙君,父亲的事、杜氏的事都是一家人的事,你有大哥、大嫂还有二哥,就算杜氏不在了,我们也会继续寻找父亲。”
随即微微哽咽:“思来思去都是杜氏,你可曾想过你自己。”
她盯着掌心的婚书,喉间泛起铁锈味,嘴角机械地往上扯,笑意像浮在水面的薄冰。
许久才听到她的声音:“可绥安己经不在了。”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